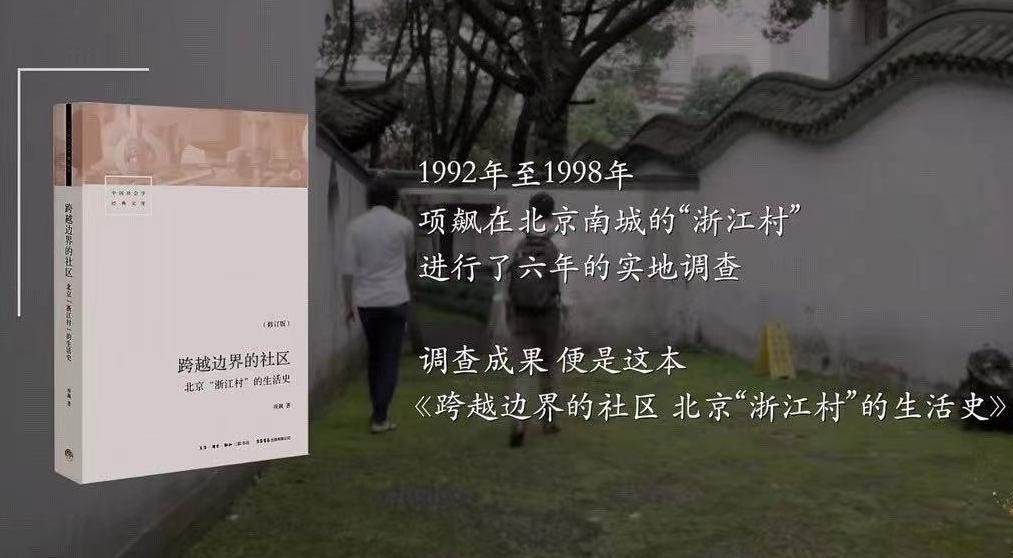这是一篇跨越两年时间的书评。
昨天看到极昼写的一篇文章《温州乐清,熬过一个缺水的冬天》,和撰稿人朋友聊了一下诞生过程。初衷是觉得很奇怪,乐清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小城镇,发生的民生新闻居然能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但后来聊着聊着,发现她的一些感受还是颇有意思。
比如现在北京疫情,记者都出不来,电话采访成为了常态。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会像乐清人一样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抵触和敌意。
「大部人在忙着赚钱,没空理我。还有些可能隐隐觉得说坏话会有风险。」她说,「也很好奇为啥温州是这样的,看到一个解释说当时永嘉学派最重视利益,宗族文化比较抱团排外。」
我回她说,温州这个社会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情与财富的金字塔”——出门靠朋友,生意靠亲戚,办事靠关系。在这种社会契约下,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人自然会有更强的距离感。
曾经我也对这些现象非常疑惑,前两年读了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是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书。所以也把两年前没写完的书评,继续写下去吧。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篇文章在高中群里引起了小规模讨论,叫做「为什么毕业后我不想回温州?| 大学生的出走与回归」。
作者是一个女生,从温中到浙大,自称经历了92年出生的这批人「最为typical」的受教育生涯(但本地人都知道,今年高考文理状元都出自温州中学,浙大又是本省唯一一家985大学——如果这种教育水平也能叫做typical,那知乎上人均985的说法也没什么问题。)
文中有个对温州非常精准的评价——「人情与财富的金字塔」。
温州是一个分化明显的城市,资源分配遵循着二八定律。 温州是一个由人情网络构成的城市,办事靠能力,但也靠人脉。 温州是一个爱面子的城市,世界太小,人比人比死人。 上一辈积累的人脉、财富甚至优质基因,在温州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印象最深的是初一那年,爷爷因病去世。
爷爷生前很聪明,却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在温州给私营老板做会计,为了多挣一些钱,一把年纪了还同时在三家公司奔波。他一生节约,在温州租了个极其廉价的简易房,通勤骑一辆老式的脚踏车。但对晚辈很大方,逢年过节回家总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印象里的爷爷很瘦削,像一只越冬归来的大雁,在自家的屋檐下回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开始一点点长大,大雁的身形也从轻巧变得笨拙。
后来爷爷得了癌症,生命的最后几年辗转于上海、温州,还有小镇上熙熙攘攘的诊所。他用顽强的意志撕裂了病理检查时最多只能活一年的死亡通知书,在死神的手掌下抗争了三年。直到后来所有治疗手段不再起效,癌细胞像黑洞一样吸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留恋。我们拔掉了插在爷爷身上的管子,把他从加护病房接回了家。在生命弥留之际,爷爷在这个家里停留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
也许是记挂爷爷在风烛残年之时还在四处奔波,也许是惦念他晚年病魔缠身的剧痛,他的两个儿子—我的爸爸和叔叔,决定给爷爷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丧事大概做了7天,丧期内每天摆10桌酒席,出殡时30桌,一共花费了几十万元。家里面摆不下这么多桌子,于是在门外搭棚子,棚子用的是那种红色的塑料布。白天亲朋好友聚集到先人的灵柩下,打牌打麻将。阳光透过棚子折射进来,照出一张张红光满面的脸;晚上开始喝酒吃大肉,筷子在一片红幽幽的烛光和银纸纷飞的火光里交错。除了摆流水席,还要做法事、请乐队,各种繁文缛节不在话下。
仔细研究一下,温州的“人情”十分复杂。范围涵盖逢年过节、子女升学、红白喜事、乔迁新居等。一个温州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基本上都是和觥筹交错的酒席绑定在一起。
- 订婚:父母见面、择下良辰吉日;男女双方准备聘礼礼金房子车子;
- 结婚:订酒桌(10年前我家办酒席,已经是一桌一万起步了。各种海参鲍鱼龙虾不在话下)。随客份子钱起步两千元,视熟悉和亲近程度再往上涨,五千至一万元也是家常便饭;
- 乔居:结婚后住进了新房,也要大张旗鼓办酒席。宾客来吃饭随份子钱,关系近的亲朋好友还要一起凑钱给主人家买家居。我家07年左右乔迁过一次,家里的大家电是爸爸的朋友出钱买的,电视机是舅舅买的(13年前上万的价格);
- 生孩子:温州人生孩子,场面不比结婚小。满月摆一次,叫“满月酒”;周岁要再摆一次,叫“对对酒”。孩子长大后升高中、大学,还要继续砸钱办酒席。
这种虽然生长于斯却维持了旁观者的疏离感,贯穿了我18岁之前的生涯。爷爷去世后的第四年,结束完高考,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泡在网上搜索北方学校的分数线。我把所有社交网络的ID改成「奔向北上广」——想要逃离南方夏天闷热潮湿的雨季,也想要挣脱小镇密不透风的人情网。小镇从此以后化为一个符号,被奋力向前奔跑的我丢在了身后。
(关于这点,之前也录过一个温州系列 的播客出走的我们,和回不去的温州,感兴趣可以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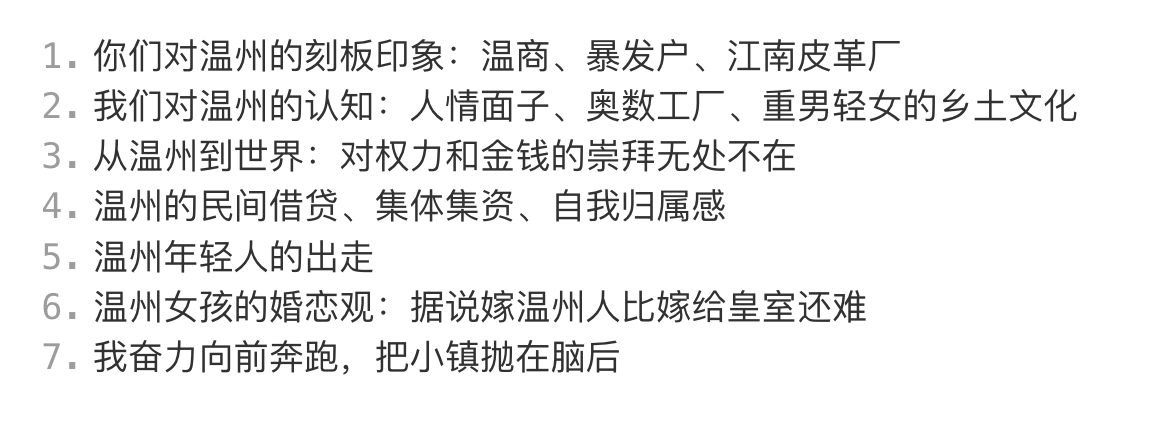
长大后读到了项飙的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很多从小到大匪夷所思的东西似乎也有了新的阐释。
项飙高中就读于温州中学,后来保送到了北大。大二期间开始立项,历经六年对“浙江村”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的田野调查,还原了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这个群体的传奇商业史和民俗志(截止到这里为止都是两年前写的,这里开始是新写的)。
问题1: 为什么温州人如何在意「关系」?
书摘:
“系”这个字最早在我脑子里冒出来,是一次在对“浙江村人”的流动史的整理过程中。很多访谈对象告诉我,他们的流动与亲友们有紧密的关系,一个带一个,呈现出典型的“链式流动”的形态。来到北京以后,同一“流动链”上的成员又在经营上合作,生活上互助,形成圈子。在早期,这就是“浙江村”基本的构成单位。用“系”这个字,多少有着“链”和“串”的意思。到后来,虽然流动超越了链式流动的方式,但人们仍然是沿着小圈子的思维来决定是否来北京以及来北京干什么。
“系”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不同关系的组合。在“浙江村”,一个系包含两个“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我叫它“亲友圈”。“亲友圈”主要包含三种关系。一是一般的亲戚;二是同村的同龄群或者同学关系;三是“文革”中的同一派系的战友。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作“生意圈”。“生意圈”里的是客户。客户是熟人,但还到不了亲友这一层。两个亚系有重叠的部分,即既是亲友,又在生意上合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
问题2: 为什么温州人四海为家全世界跑?
在欧洲,温州面馆到处都是;在全国各地,浙商也遍地开花。为什么温州人这么喜欢往外跑呢?小时候有本书叫《话说温州》,里面写说因为温州「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穷乡僻壤经济发展不出来,逼得温州人只能出了山四处做生意。而这本书里有了另外的解释。


书摘:
“你们读书人应该知道的,按我们拆字的办法说,运道运道,运动起来,才有这个道。”关于生意的“运道”的观点及对“运道”的这种解释,真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流动文化”了。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角度看,又能得出另一种解释。当温州人在一地聚居到一定程度,由于他们从事的产业很雷同,竞争势必加剧,为降低竞争、保持利润率,就要开拓新的领地。
“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的小企业难以迅速发展,是因为中国人只信任自己的人,而不欢迎专业的管理者。
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在“浙江村”和“流动经营网络”形成的中早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我们可以把扩散流动看作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
问题3: 为什么温州人这么爱在外面跑,还如此有「家」的宗族观念?
”根据1996年虹桥镇的统计数字,该镇共24581户,88293人。劳动力33567,外出10429,出省的9720人。
这3位被访者的茫然神情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真要返回,在村里能找到现成的经济机会吗?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再返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
问题4: 为什么温州人有如此复杂的繁文缛节?
前面说过温州人有非常多的礼俗。关于这一点,我之前和朋友录过一期播客当一个女性主义者遇上清朝式温州婚礼,感兴趣可以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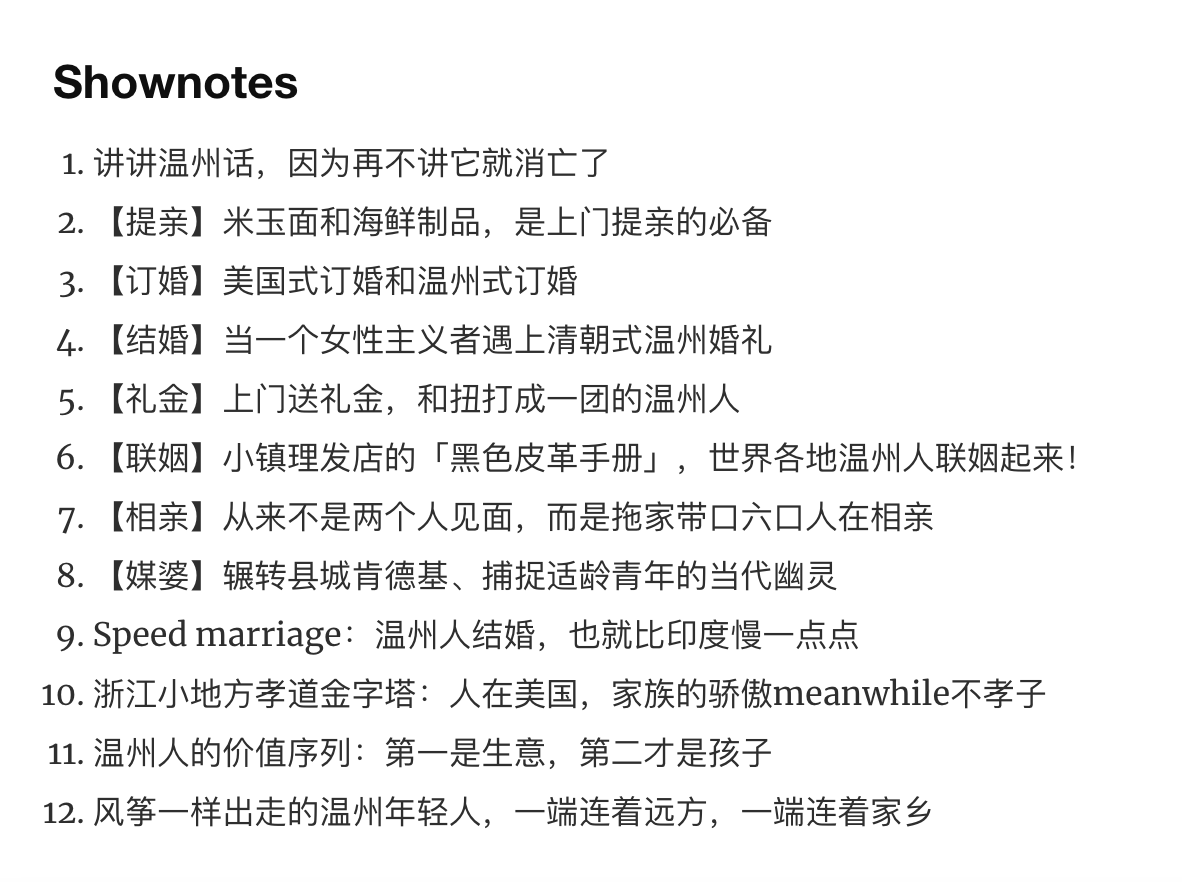
书摘:
“印”是“明显的痕迹”的意思。比如一个盛热水的水杯子在塑料布上烫了一个圈,这个痕迹叫“印”。在用“印”这个字的时候,人们并不强调痕迹本身,而是要强调“曾有一个水杯在这里出现过”——“你看,印还在这里呢!”对人们的流动有直接影响的乃是这个家族之印,精确地说,是“家族关系”,而不是家族本身。
同时,他们毕竟需要操作一些文化仪式来强化他们流动中的关系,毕竟需要一些仪式来表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于是家族的“印”又成了他们的依托。
问题5: 温州人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
那位写缺水的朋友聊到说,采访过程中发现,乐清人会把缺水归结于「天灾」和「命数」,并且好几个人会强调说「政府已经非常努力了」。她说「他们习惯在现有环境里求生存,不太想环境里有哪些部分本可以更好、能够改变」,我说「小地方的人,有着本能的卑微和顺从」。
小时候的地方课本,似乎都在强调温州是个自力更生的地区。政府没钱修公路,就自己赚钱修;政府不给造动车站,就老乡自己集资建。温州人和政府、和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书摘:
“浙江村”的拉锯战让我们想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人们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合法修改权只掌握在国家手中时,他会怎么办呢?
我们曾关注到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退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
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
Hirschman(1970)提出了“退出”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的关系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的物品、组织与制度。
如果把Hirschman的概念拓展到社会学研究领域,那么以上三种策略就可以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所谓“民主国家”中发生的,像表达与退出;另一类则是在所谓极权社会中发生的,如变通。事实上,变通也正是被视为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
(插一句,这一点我不是很同意。明明在极权社会里,「退出」才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吧。)
逃跑,是“浙江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不放弃对权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那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除了这两种较极端的类型之外,还有没有中间类型的行为策略?第二,除了这些与其背景性的结构相统一、相整合的行为方式(比如表达行为与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是同一事实的两面)之外,还有没有与现行结构并不完全统一,可能导致结构性变迁的行为策略?
“浙江村”的“逃跑”提醒我们在事实中还存在另一个策略:逃避。它与表达、变通不同。它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行制度既不寻求连名带实的改变,也不期望暗度陈仓、偷梁换柱,而是采取漠然的态度。如果说表达和变通都是要通过与国家的不同部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积极互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逃避则尽量不与国家发生正面的关系。它要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逃避与退出的区别在于,退出的实质是一种制度安排,“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行为本身远要重要;而逃避是不为制度所认可的,它就是行为本身。
问题6: 温州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参与家乡的建设?
温州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城市/村镇里的很多公共设施(本应由政府来承建的项目),都是私人自发集体性行为。比如说庙宇修建、街道整修等等,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书摘:
过去温州人身处异地,环境的猛然转变,新环境下社会控制和长远规划的缺失,使人们仿佛驶进了波涛汹涌又不见航标的海面,而在原社区形成的传统道德意识,只能如单薄的小木舟,分崩离析,化为木屑。所谓社会转型期间,容易出现道德“失范”,也是这个道理。现在温州人看到了航标,也驶进了平静的港湾,眼明则心亮,也就需要一种有序的生活。爱心成了他们新的追求。
要让温州人在这里认识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能自觉地为集体着想(尽管最后还有利于促进个人利益),这在过去也不可能。温州人现在所以愿意这么做,除了直接的利益考虑外,也是在追求一种“归属感”。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当人发现自己什么群体都不属于时,他就成了所谓“边缘人”或称“边际人”,十分痛苦。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积极地修桥补路、捐建庙宇,其前提是: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是这一大群人里的一分子;潜意识中的目的是:我要通过公共事业,与这个地方更紧密地联在一起,在这群人中得到更高的认同。
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当人发现自己什么群体都不属于时,他就成了所谓“边缘人”或称“边际人”,十分痛苦。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积极地修桥补路、捐建庙宇,其前提是: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是这一大群人里的一分子;潜意识中的目的是:我要通过公共事业,与这个地方更紧密地联在一起,在这群人中得到更高的认同。有形依托(指京温市场)的生成和政府思路的变化,使“浙江村人”重新有了“归属感”!
好了不写了,就到这里吧。
由于公众号被封之后,我一直懒得开新号,而 telegram 没有赞赏功能。如果你喜欢本期 blog,欢迎请我喝杯咖啡。
爱发电:https://afdian.net/a/Hayami
Patreon:https://www.patreon.com/hayami_kira
支付宝